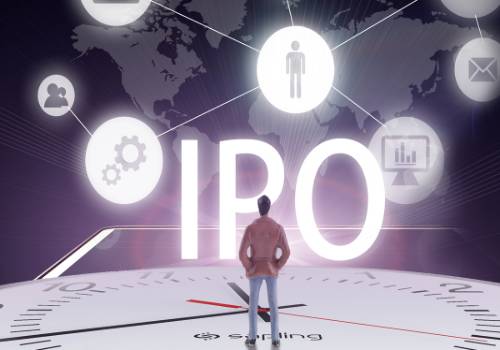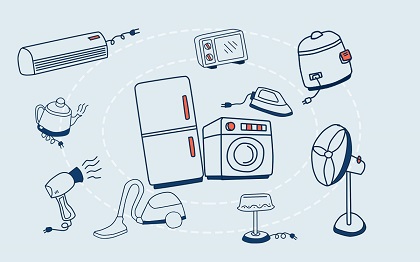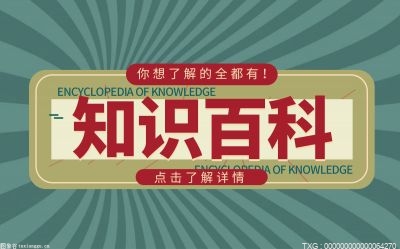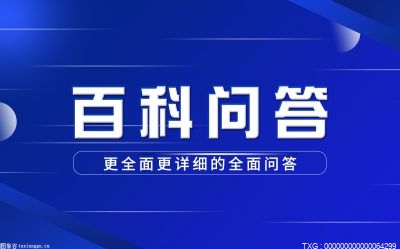來源:中國(guó)社會(huì)科學(xué)網(wǎng)-中國(guó)社會(huì)科學(xué)報(bào) 時(shí)間:2023-08-31 10:44:59
作者:羅久(西安電子科技大學(xué)人文學(xué)院哲學(xué)系副教授)
德國(guó)浪漫主義是18世紀(jì)末19世紀(jì)初歐洲興起的一場(chǎng)重要思想文化運(yùn)動(dòng)。早期浪漫主義者敏銳地覺察到現(xiàn)代人類與自然的持續(xù)疏離和對(duì)立,他們對(duì)人類中心論的理性主義形而上學(xué)、近代的科學(xué)觀念及其研究方法,以及資本主義商品經(jīng)濟(jì)的整體性批判,深刻地揭示或者說預(yù)見了現(xiàn)代生態(tài)危機(jī)之所以產(chǎn)生的內(nèi)在根源。以諾瓦利斯為代表的早期浪漫主義者試圖重新喚起一種以情感、精神和具體的感性存在為中心的活生生的自然的形象,以取代啟蒙理性和現(xiàn)代科學(xué)對(duì)一種關(guān)于自然的單純的可量化的、排除了一切感性存在的、確定的理性知識(shí)的關(guān)注;用詩(shī)意的言說取代理性的分析和推理,將人和自然之間存在的主體對(duì)客體的壓制關(guān)系轉(zhuǎn)化為一種平等的“我—你”關(guān)系,恢復(fù)自然作為自發(fā)的、能動(dòng)的、創(chuàng)造性主體的地位。
 【資料圖】
【資料圖】
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(xué)與自然的消亡
早期浪漫主義者將以費(fèi)希特為代表的主體主義哲學(xué)視為現(xiàn)代生態(tài)危機(jī)的思想根源。在費(fèi)希特的知識(shí)學(xué)中,“自我”與“非我”的區(qū)分構(gòu)成了一個(gè)基本的二元區(qū)分。對(duì)費(fèi)希特來說,自我的本質(zhì)是行動(dòng),行動(dòng)受理性和意志的指導(dǎo),而非我缺乏任何實(shí)質(zhì)性的規(guī)定,非我的存在或“非我是非我”完全是作為“我是我”的反設(shè)定才能得到理解。因此,非我不具有任何實(shí)在性,而自我通過一種永恒的努力來設(shè)定非我和非我與自我的統(tǒng)一,從而證明自我本身的絕對(duì)性。無論非我是什么,它都只是自我行動(dòng)的結(jié)果。費(fèi)希特認(rèn)為,自我的最終任務(wù)是通過實(shí)踐行動(dòng),在更大程度上將非我統(tǒng)一于自我。因此,自我應(yīng)該支配非我是費(fèi)希特哲學(xué)體系的直接結(jié)果。這一觀點(diǎn)對(duì)人與自然的關(guān)系具有深遠(yuǎn)的理論和實(shí)踐意義。
按照費(fèi)希特的想法,自然只不過是非我,是依賴于自我設(shè)定自我的一種反設(shè)定。自然只能被視為在根本上依賴于人類自我意識(shí)的被動(dòng)的對(duì)象。自然中不可能意識(shí)到自我,自然本身也不可能具有任何形式的自發(fā)性。這種對(duì)自然的理解適用于無生命的自然,也適用于動(dòng)植物,甚至適用于具有身體和物質(zhì)性要素的人本身。這種對(duì)待自然的態(tài)度早在弗朗西斯·培根那里就已經(jīng)提出了,而費(fèi)希特的自我意識(shí)理論使自然在本體論上完全成為自我的附庸。
費(fèi)希特的觀點(diǎn)體現(xiàn)了現(xiàn)代科學(xué)、技術(shù)和經(jīng)濟(jì)過程中所表達(dá)的鮮明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(chǎng)的哲學(xué)根源。盡管在許多方面,德國(guó)浪漫主義者從費(fèi)希特的知識(shí)學(xué)中吸收了很多重要思想,但他們一致批評(píng)他對(duì)自然的理解。例如,謝林在思考費(fèi)希特的哲學(xué)時(shí)就曾經(jīng)說過,“所有現(xiàn)代哲學(xué)都以一種仿佛自然不存在的方式進(jìn)行”。在謝林看來,費(fèi)希特的知識(shí)學(xué)像笛卡爾以來大多數(shù)理性主義和主體性哲學(xué)一樣,不能把自然看作一個(gè)獨(dú)立的實(shí)體,甚至比笛卡爾更加徹底地取消了自然的本體論地位。諾瓦利斯也同樣意識(shí)到,只要自然被視為非我,自然本身的生命力和它的獨(dú)立性就無法得到充分理解,甚至?xí)獾交诂F(xiàn)代的主體性原則的理論和實(shí)踐計(jì)劃的毀滅性打擊。這尤其表現(xiàn)在諾瓦利斯對(duì)現(xiàn)代科學(xué)的批判中:“友善的自然在自然科學(xué)家的手下死了,留下的只是沒有生命的、抽搐的殘骸。”
在一個(gè)不同的比喻中,諾瓦利斯把作為科學(xué)研究對(duì)象的自然比作一個(gè)“石化了的被施了魔法的城市”。因此,科學(xué)不可能對(duì)自然做出任何充分的斷言。這種斷言的對(duì)象不是自然本身,而是處于石化和死亡狀態(tài)的自然。諾瓦利斯說:“追求真理的一切努力在關(guān)于自然的講演和談話中只是越來越遠(yuǎn)離自然性。”所有關(guān)于自然的演講和對(duì)話的問題在于它是關(guān)于自然的,而自然本身并沒有語言,也不參與這種對(duì)話。一旦我們談?wù)撟匀唬筒辉僮鳛樽匀欢嬖冢皇亲鳛槿祟愐庾R(shí)的一個(gè)對(duì)象,是一個(gè)被人的理性的概念、命題和數(shù)學(xué)的語言重新闡釋和建構(gòu)起來的對(duì)象。
詩(shī)與自然的內(nèi)在生命
主體性哲學(xué)傳統(tǒng)用自我和他者、自我和非我這樣一些分離的范疇來描述精神和自然之間的區(qū)別。諾瓦利斯雖然采用了這些范疇,但是在一個(gè)動(dòng)態(tài)的交互關(guān)系中改變了它們的意義:具有自我意識(shí)的人類必須既被視為自我,又被視為他者;而自然必須既被視為他者,又被視為自我。這尤其意味著精神的概念不只是為人類保留的,精神也適用于自然。自然和人類一樣,都具有能動(dòng)的、自發(fā)的、自我組織的精神層面。這種恢復(fù)自然本身的實(shí)體性和內(nèi)在活力的觀點(diǎn)使得心靈與物質(zhì)、精神與自然的統(tǒng)一成為可能。因此,諾瓦利斯拒絕像費(fèi)希特那樣將自然理解為非我。如果自然是活生生的、能動(dòng)的存在,也即某種意義上的行動(dòng)者或者“我”,那么我們就不能像費(fèi)希特那樣將自然轉(zhuǎn)化為一種無限異于“自我”的“非我”,而是必須將自然轉(zhuǎn)化為一個(gè)“你”——我們能夠與之處于對(duì)話之中并彼此呼應(yīng),因而我們能夠在自然中有“在家”之感。“人類并非獨(dú)自言說——宇宙也在言說——萬物皆在言說——無限的語言。”
人類理性的本性有一種通過反思和概念性的思維將自身與感性的、多樣性的、變動(dòng)不居的自然分離開來的傾向,用純?nèi)焕硇缘恼Z言來言說自然,從而使自然變成了一個(gè)無聲的他者。諾瓦利斯認(rèn)為,哲學(xué)家和科學(xué)家沒有能力來聆聽自然的言說,因?yàn)樗麄儾皇前炎匀蛔鳛橐粋€(gè)同樣具有自我意識(shí)的主體、一個(gè)平等的對(duì)話者,而是作為一個(gè)全無意識(shí)和生命的惰性的物質(zhì)世界、一個(gè)完全受制于主體的客體;只有詩(shī)人具有克服這種分離的能力。在諾瓦利斯看來,詩(shī)人的一個(gè)特征是他對(duì)自然的熱愛賦予自然更多的靈性:“誰想真正了解自然的心緒,誰就必須和詩(shī)人待在一起。在那里,自然敞開她的心扉,傾吐她奇妙的心聲。但是,誰若不是發(fā)自內(nèi)心地?zé)釔圩匀唬皇求@異于自然的一部分或者另一部分,并意在從中獲取經(jīng)驗(yàn),他就只能勤于造訪她的病房或者她的尸骨存放所。”
對(duì)諾瓦利斯來說,真正的詩(shī)人不僅是,或者說主要并不是指一種特定體裁的文學(xué)作品的創(chuàng)作者。詩(shī)人的主要特征是,他有能力發(fā)現(xiàn)自然,這個(gè)看似無意識(shí)的他者實(shí)際上是與“我”相對(duì)應(yīng)的“你”,即另一個(gè)有生命、有意識(shí)的主體。這種對(duì)自然作為“你”的完全承認(rèn)意味著對(duì)自然的愛,也就是在自然中發(fā)現(xiàn)了另一個(gè)活生生的、能夠與之共情的自我。從某種意義上說,愛的神秘之處在于它不試圖決定對(duì)方,而是接受對(duì)方的不可規(guī)定性,接受對(duì)方自身的發(fā)展。
在諾瓦利斯看來,不同于科學(xué)在追求關(guān)于自然的理性認(rèn)識(shí)時(shí)將自然固化在理性的確定性之中,詩(shī)人能夠遵循自然的不可由理性規(guī)定的、不確定的、流動(dòng)的和變易的運(yùn)動(dòng)。不僅如此,詩(shī)人還具有獨(dú)特的創(chuàng)造力。在這種創(chuàng)造性中,他展示了自己與自然之間的內(nèi)在聯(lián)系。因?yàn)樵谠?shī)人的體驗(yàn)中,自然就其自身而言本質(zhì)上是創(chuàng)造性的。詩(shī)人的心靈比自然科學(xué)家更加敏感,情感更加充沛,更加富有想象力,他在自然不可分解和不可還原的整體性中來理解自然的現(xiàn)象,他能夠表達(dá)自然本身試圖以某種非理性的形式向我們顯現(xiàn)出來,卻被理性的思維所消解和掩蓋起來的真理。
對(duì)自然的詩(shī)意言說是對(duì)自然本身的言語的聆聽,而在這種詩(shī)意的言說當(dāng)中,詩(shī)人是將自然作為另一個(gè)自我、一個(gè)“你”來看待;詩(shī)人承認(rèn)自然具有無法被我們的理性思維所規(guī)定的獨(dú)立性,甚至在對(duì)自然的聆聽中心甘情愿地舍棄自身的獨(dú)立性,而這種人與自然之間的關(guān)系,即對(duì)自然的尊重和同情的完美形式就是“愛”。從諾瓦利斯的意義上來說,愛并不只是一種存在于人與人之間的情感;在愛之中,人在自然中看到了人性,同樣也意識(shí)到人性與自然不可分割的統(tǒng)一性。在與自然的對(duì)話中,人類將自己的所有活動(dòng)視為自然創(chuàng)造力的表現(xiàn)。因此,人類所創(chuàng)作的詩(shī)雖然表面上不同于自然的創(chuàng)造力,但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視為自然本身的表達(dá),是對(duì)自然本身的真理的揭示或再創(chuàng)造。
對(duì)諾瓦利斯來說,詩(shī)是在人與自然之間進(jìn)行聯(lián)結(jié)的紐帶。通過這個(gè)概念,諾瓦利斯表達(dá)了他對(duì)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的看法:真正成為人、成為具有自我意識(shí)的精神性存在并不意味著與自然的對(duì)立和對(duì)自然的支配,而是在詩(shī)意的言說中聆聽自然的語言,恢復(fù)因主體性的反思哲學(xué)和科學(xué)解釋而被打破的一種普遍的和諧:“詩(shī)通過使一物與整體中的其余部分的特定結(jié)合提升了每一個(gè)單獨(dú)的事物——如果是哲學(xué)首先通過它的立法為觀念的積極影響準(zhǔn)備了世界,那么,詩(shī)可以說是哲學(xué)的關(guān)鍵,它是世界的目的和意義;因?yàn)樵?shī)塑造了美麗的社會(huì)——世界大家庭——美麗的宇宙之家。”通過將人類作為“自然存在”與一種無限的積極的創(chuàng)造力的觀念重新整合起來,浪漫主義者拒絕了啟蒙運(yùn)動(dòng)所宣揚(yáng)的人類相對(duì)于自然的主導(dǎo)地位。
現(xiàn)代經(jīng)濟(jì)與生態(tài)危機(jī)
人與自然關(guān)系的一個(gè)關(guān)鍵點(diǎn)是人類的經(jīng)濟(jì)行為和態(tài)度如何考慮或影響自然。諾瓦利斯非常清楚這個(gè)實(shí)際問題的重要性。諾瓦利斯并不是封建小農(nóng)經(jīng)濟(jì)和行會(huì)制度的擁護(hù)者;相反,他充分認(rèn)識(shí)到現(xiàn)代商品經(jīng)濟(jì)的創(chuàng)造性和它在促進(jìn)人類共同體的形成方面的積極作用:“商業(yè)精神就是世界的精神。這是它們之中最燦爛的精神。它使一切都運(yùn)轉(zhuǎn)起來,并將一切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它喚起了國(guó)家和城市、民族和藝術(shù)作品。它是文化的精神,是人類的完成。”每當(dāng)商品被發(fā)明和生產(chǎn)出來,經(jīng)濟(jì)就成為人類創(chuàng)造力的一種表現(xiàn)。只要經(jīng)濟(jì)活動(dòng)需要討價(jià)還價(jià)和貿(mào)易,它就是交流的手段和原因,是接近他人和與他人交換的方式。當(dāng)人與人之間的經(jīng)濟(jì)關(guān)系以及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經(jīng)濟(jì)關(guān)系受到一種相互需要和共屬一體的愛的精神的支配時(shí),這樣一種詩(shī)意的經(jīng)濟(jì)將使經(jīng)濟(jì)與自然的和諧成為可能,而整個(gè)經(jīng)濟(jì)過程將成為自然本身創(chuàng)造力的表現(xiàn)。
不過,諾瓦利斯清楚地認(rèn)識(shí)到,實(shí)際存在的資本主義經(jīng)濟(jì)行為所隱含或者預(yù)設(shè)的貪婪的人性、私有財(cái)產(chǎn)的觀念以及自利的基本傾向,與詩(shī)意的經(jīng)濟(jì)是完全不相容的。它阻礙了人類和社會(huì)的完善,使人類難以找到與自然和諧相處之道,成為導(dǎo)致現(xiàn)代生態(tài)危機(jī)的一個(gè)重要根源。
諾瓦利斯在他的小說《海因里希·馮·奧弗特爾丁根》中展示了世界的和諧秩序是如何被貪婪摧毀的。如果一個(gè)人被貪婪所統(tǒng)治,他就會(huì)站在所有和諧之外,與愛和詩(shī)意的生活發(fā)生沖突。此外,在諾瓦利斯看來,私有財(cái)產(chǎn)的觀念導(dǎo)致對(duì)自然的漠視,并最終導(dǎo)致占有者本人的毀滅:“大自然不希望被某一個(gè)人獨(dú)占。作為財(cái)產(chǎn),自然變成了一種邪惡的毒藥,驅(qū)走寧?kù)o,使那些擁有財(cái)富的人毀滅性地貪戀對(duì)萬物的權(quán)力,帶來一系列無盡的憂慮和狂野的激情。因此,自然暗中破壞占有者的土地,使它很快塌陷并埋葬他,這樣她可以從一只手傳到另一只手,從而逐漸滿足她屬于每個(gè)人的傾向。”
諾瓦利斯對(duì)私有財(cái)產(chǎn)的批判性觀點(diǎn)源自他的哲學(xué)思想,即自然被理解為“你”。“你”作為另一個(gè)活生生的“自我”不能作為財(cái)產(chǎn)被占有,可是當(dāng)現(xiàn)代人將財(cái)產(chǎn)權(quán)的觀念強(qiáng)加于自然之上時(shí),自然確實(shí)變成了一個(gè)只能被人的理性所描述、計(jì)算和支配的“非我”。作為“你”的自然需要得到尊重和承認(rèn),這種尊重和承認(rèn)的完美形式是愛。對(duì)諾瓦利斯來說,理想的社會(huì)以及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完美和諧,是基于愛的理念。很明顯,愛的對(duì)立面是純粹的自利。自利與詩(shī)意的經(jīng)濟(jì)是不相容的。然而,在諾瓦利斯時(shí)代,自利卻越來越被視為所有經(jīng)濟(jì)行為的出發(fā)點(diǎn)和本質(zhì)。事實(shí)上,自利已經(jīng)成為現(xiàn)代西方經(jīng)濟(jì)和現(xiàn)代經(jīng)濟(jì)思想的基礎(chǔ)之一。
現(xiàn)代經(jīng)濟(jì)盡管在發(fā)明和生產(chǎn)方面似乎具有高度的創(chuàng)造性,卻不能稱之為諾瓦利斯意義上的詩(shī)意的經(jīng)濟(jì)。它的創(chuàng)造力沒有對(duì)自然的尊重和承認(rèn),它沒有與對(duì)自然的熱愛相結(jié)合。它不是把自然當(dāng)作一個(gè)“你”,而是當(dāng)作一個(gè)“非我”。因此,從諾瓦利斯的角度來看,這種形式的創(chuàng)造并沒有導(dǎo)致人類與自然的融合,而是導(dǎo)致了對(duì)自然的漠視和壓迫。現(xiàn)代經(jīng)濟(jì)生產(chǎn)的基礎(chǔ)不是熱愛自然和以自然為導(dǎo)向,而是以自利和收益的最大化為導(dǎo)向。因此,人類迷失在無休止和無意義的消耗自然、擴(kuò)大生產(chǎn)、增加收益的進(jìn)步強(qiáng)制當(dāng)中。就此而言,現(xiàn)代資本主義商品經(jīng)濟(jì)的基礎(chǔ)本身就構(gòu)成了現(xiàn)代生態(tài)危機(jī)問題的一部分。
現(xiàn)代科技和資本主義的發(fā)展對(duì)自然造成了不可逆轉(zhuǎn)的破壞,隨之產(chǎn)生了日益嚴(yán)重的生態(tài)危機(jī),德國(guó)浪漫主義的哲學(xué)反思越發(fā)具有了不容忽視的現(xiàn)實(shí)意義。諾瓦利斯對(duì)現(xiàn)代生態(tài)危機(jī)的浪漫主義反思不是懷舊的或者烏托邦式的。相反,他充分認(rèn)識(shí)到現(xiàn)代科學(xué)和商品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的合理性與現(xiàn)實(shí)性,并試圖通過對(duì)其形而上學(xué)基礎(chǔ)的批判,揭示被現(xiàn)代科學(xué)和經(jīng)濟(jì)的合理性模式所掩蓋和歪曲的人性以及自然本身的內(nèi)在生命力,從而為我們思考現(xiàn)代生態(tài)危機(jī)的根源及其解決之道提供了一個(gè)獨(dú)特且發(fā)人深思的洞見。
標(biāo)簽:
- 加強(qiáng)注重產(chǎn)品質(zhì)量管控,鄭州膏藥提升用戶體驗(yàn)
- 絕殺?李可精準(zhǔn)直塞獻(xiàn)助攻,姜祥佑第87分鐘單刀破門
- 今日熱門!水費(fèi)人工查詢電話 昆明水費(fèi)人工查詢電話
- 北京國(guó)際展覽中心2023展會(huì)時(shí)間表_北京國(guó)際展覽中心 熱訊
- 北交所新三板出臺(tái)“十八條”優(yōu)化市場(chǎng)服務(wù) 環(huán)球時(shí)訊
- 5月31日中獸醫(yī)分會(huì)|犬瘟熱臨證概論
- 陜西省岐山縣發(fā)布暴雨藍(lán)色預(yù)警_熱點(diǎn)
- 【速看料】積極投身志愿服務(wù)
- 視點(diǎn)!湖北五峰后河國(guó)家級(jí)自然保護(hù)區(qū)發(fā)現(xiàn)4個(gè)新物種
- 枇杷園_關(guān)于枇杷園概略
- 天天關(guān)注:重慶6區(qū)縣出現(xiàn)暴雨 13條中小河流漲水
- 臺(tái)風(fēng)“瑪娃”已造成日本1死30傷,178棟住宅受損
- 安吉韓都生活家居有限公司_天天視訊
- 西方國(guó)家向非洲轉(zhuǎn)移垃圾
- 白羊男和獅子女的結(jié)局 是正緣! 環(huán)球快播報(bào)
- 長(zhǎng)沙南站到常德多少公里_長(zhǎng)沙南站到常德-通訊
- 隋朝開國(guó)時(shí)的都城是什么-隋朝開國(guó)都城-焦點(diǎn)簡(jiǎn)訊
- 白鹿原白靈兒_白鹿原白靈 天天資訊
-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是什么意思一年級(jí)-當(dāng)前報(bào)道
- 【世界新要聞】對(duì)稱矩陣的定義及性質(zhì)_對(duì)稱矩陣的定義
- 微信不能發(fā)語音怎么設(shè)置 oppo 微信不能發(fā)語音怎么設(shè)置
- 鄭州仙佑:膏藥行業(yè)拓展品牌文化內(nèi)涵,提升品牌影響力
- 中篇小說《九重葛》講了些啥?作家邵麗傾情解讀
- 選對(duì)番茄醬=拿捏住了意式披薩的靈魂
- 武漢理工大學(xué)卜童樂研究員在鈣鈦礦電池模組制備技術(shù)上取得新進(jìn)展
- 北白犀還有救嗎?只剩最后兩頭,都是母的,護(hù)衛(wèi)24小時(shí)帶槍保護(hù)
- 實(shí)驗(yàn)猴一只16萬元,藥企瘋狂“囤猴”!發(fā)生了什么?
- 33億光年外,中國(guó)天眼重大發(fā)現(xiàn),或?qū)⑵平庥钪娴囊粋€(gè)謎題
- 中科院取得多模態(tài)神經(jīng)感知研究進(jìn)展,有助研發(fā)高智能機(jī)器人
- 風(fēng)電機(jī)成新頂級(jí)食肉動(dòng)物,絞殺1300只猛禽,還有必要發(fā)展風(fēng)電嗎?
- 日本理化所利用量子化學(xué)機(jī)器學(xué)習(xí),熒光分子合成成功率75%
- 3年、5年、7年以上的老巖茶,適合新手嗎?巖茶怎么入門比較好?
- 發(fā)現(xiàn)“天馬”!拍到多只“麒麟獸”中華鬣羚,體高腿長(zhǎng)有獸角
- 中國(guó)天眼每天要花40萬,位于貴州山區(qū)的它,目前都發(fā)現(xiàn)了什么
- 峨眉山“人猴大戰(zhàn)”頻發(fā),從靈猴淪為“街溜子”,到底是誰的錯(cuò)?
- 排隊(duì)四小時(shí)的新式茶飲,需要新故事
- 江西人點(diǎn)的宴客菜,看完終于明白:為啥江西人被叫“辣不怕”了
- 可再生能源新寵兒?華人科學(xué)家“變廢為寶”,或?qū)⒔鉀Q百年難題
- “昨天喝多了把這個(gè)扛回家了,現(xiàn)在醒酒了我該怎么辦?”哈哈哈
- 江西各地級(jí)市的“市樹、市花”,你都知道嗎?
- 西雙版納發(fā)現(xiàn)“森林精靈”,長(zhǎng)得像老鼠又像小鹿,比大熊貓稀有
- 長(zhǎng)頸鹿脖子為何那么長(zhǎng)?為了吃嗎?科學(xué)家:有利于找對(duì)象
- 宇宙深空一直發(fā)射著神秘信號(hào),每16天出現(xiàn)一次,是誰發(fā)出的?
- 芒種前后,這5種美食別錯(cuò)過,應(yīng)季而食營(yíng)養(yǎng)高,早吃早受益
- 方太:有一種勇氣叫“從零到一”
- 高考倒計(jì)時(shí),做幾款童趣早餐,給孩子解解壓!營(yíng)養(yǎng)簡(jiǎn)單娃喜歡!
- 長(zhǎng)點(diǎn)兒心吧!別花冤枉錢了,你以為喝著正品紅牛,其實(shí)是侵權(quán)的
- “玉兔精”李玲玉教人做菜,用名貴紅酒煮一顆梨,被質(zhì)疑太奢侈
- “時(shí)間”是否存在,一名女性在洞穴中住130天,科學(xué)家得出結(jié)論
- 醫(yī)藥生物行業(yè)專題報(bào)告:mRNA技術(shù)有望迎來黃金十年
- 我國(guó)口服抗癌疫苗基礎(chǔ)研究取得新進(jìn)展
- 炒肉時(shí),牢記4個(gè)技巧,不管炒什么肉都鮮嫩多汁,不腥不柴還入味
- 美國(guó)科學(xué)家:土衛(wèi)六和地球相似度極高,但它太奇怪了
- 外星人為何沒造訪地球?美科學(xué)家:外星文明太發(fā)達(dá)陷危機(jī),不來了
- “每天二兩醋,不用去藥鋪”?沒事吃點(diǎn)醋,身體或收獲這些好處
- 老虎的吼叫,能麻痹動(dòng)物,它會(huì)在捕獵過程中當(dāng)“定身術(shù)”用嗎?
- 重磅!湯加火山爆發(fā)為百年來最猛烈,對(duì)全球氣候的影響值得再研究
- 3根排骨1包醬,這一個(gè)做法廣東人百吃不膩,每一次做吃完還舔舔手
- 蚊子最大的天敵,竟然不是蚊香?別不相信!只需5分鐘蚊子消失了
- 月球上豎立五星紅旗,美國(guó)登月再被質(zhì)疑,美國(guó)國(guó)旗為何在飄動(dòng)?
- 對(duì)標(biāo)傳統(tǒng)儲(chǔ)存方案,一克可儲(chǔ)存2.15億GB數(shù)據(jù)!DNA儲(chǔ)存時(shí)代到來?
- 南方人的寶貝,北方人聽名字就嚇一跳!香甜軟糯一口淪陷!
- 4款“奶奶輩”的傳統(tǒng)糕點(diǎn),都是兒時(shí)記憶中的味道,看看你吃過嗎
- 狗子被主人“養(yǎng)熟”,一般有這7個(gè)信號(hào),別后知后覺
- 不明原因兒童急性肝炎與新冠有關(guān)?柳葉刀子刊最新研究激起千層浪
- 蚊子最大的天敵,竟然不是蚊香?別不信,只需5分鐘蚊子“不見了”
- 新冠病毒在野生動(dòng)物中傳播,意味著什么?會(huì)傳染給人類嗎?
- “注膠肉”已泛濫,大多存在這3種肉當(dāng)中,別再買錯(cuò)
- 哪些女性適合剖腹產(chǎn)?寶寶的第一口應(yīng)該吃什么?
- 人類是茫茫宇宙唯一的智慧文明嗎?不然會(huì)什么會(huì)一直找不到外星人
- 26000萬光年外,質(zhì)量是太陽的400萬倍,巨大黑洞會(huì)吞噬地球嗎
- 東莞理工學(xué)院科研團(tuán)隊(duì)提出短期電力負(fù)荷預(yù)測(cè)的新方法
- 沒想到四川人這么愛吃甜,看過四川的“8大甜食”,真甜到心里
- 中科院院士相信外星人存在?53年前的一塊小隕石,能證明他的觀點(diǎn)
- 螺螄怎么做才好吃?大廚教你正確做法,麻辣鮮香,解饞過癮
- 小看了日本?日科學(xué)家搞定海水淡化實(shí)驗(yàn),全球幾十億人有福了
- 1.6米長(zhǎng)的“吃人鱷”現(xiàn)身蘇州,重15公斤,人為放生的概率最大?
- 鵪鶉蛋放鍋里一蒸,想不到這么好吃,好多人不知道的做法,真香
- 原來水不是只有固態(tài)、液態(tài)和氣態(tài),“第四種水”在深海中被發(fā)現(xiàn)
- 黑猩猩奧利弗:個(gè)別染色體發(fā)生突變,與人類基因相似性只差1.2%
- 沖泡白茶餅的5個(gè)步驟,簡(jiǎn)單好學(xué)又能喝到好茶,行家天天都在用
- 廈門這家私房潮州菜人均600+,鮑參翅肚十余種做法,還可飲茶撫琴
- 最近迷上這早餐,一次蒸2大鍋,口味多多不重樣,天天都能睡懶覺
- 喜歡吃藍(lán)莓,自己在家養(yǎng),一棵能摘一大筐,好吃又營(yíng)養(yǎng)
- 喵星人與汪星人,祖先是野生動(dòng)物,一本繪本讀懂家養(yǎng)動(dòng)物馴化史
- 抱著愛犬睡了一整晚,一早醒來卻發(fā)現(xiàn)這是一只陌生汪!
- 火星上發(fā)現(xiàn)“石門”?看起來像人造結(jié)構(gòu),NASA:好奇號(hào)火星車拍攝
- 在睡夢(mèng)中到達(dá)木衛(wèi)四!未來的星際旅行會(huì)在冬眠中進(jìn)行嗎?
- 饅頭不蓬松?試試加點(diǎn)它!細(xì)膩柔軟香味濃,比白面饅頭滋潤(rùn)!
- 建議大家,若不差錢,多囤這5款“純糧好酒”,家里長(zhǎng)輩都愛喝
- 石榴貴族——突尼斯石榴,價(jià)格比普通石榴貴多了,我們要怎么種?
- 榴蓮如何挑選?別只會(huì)挑圓的,牢記3個(gè)小技巧,挑榴蓮不發(fā)愁了
- 自己做面包,一滴水不用放特簡(jiǎn)單,暄軟好吃鈣質(zhì)高,比買的好多了
- 它是“天然抗菌劑”殺菌防感冒,這季節(jié)別錯(cuò)過,多買些儲(chǔ)存慢慢吃
- 罕見!浙江九龍山拍到黃喉貂,個(gè)頭不大卻是野豬天敵,行蹤很神秘
- 蚊子最怕的東西,竟然不是蚊香?你別不信,只需5分鐘蚊子消失了
- 80年代很火的“白皮黃瓜”,為啥后來遭淘汰了?答案讓人意外
- 廣州市白云區(qū)有一家“網(wǎng)紅”餐廳,招牌是螺螄粉,幾乎天天都排隊(duì)
- 土衛(wèi)六天然氣是地球的數(shù)百倍,儲(chǔ)量豐富,如果不小心點(diǎn)燃會(huì)怎樣?
- 自從學(xué)會(huì)了這小點(diǎn)心,孩子三天兩頭點(diǎn)名要吃,香甜酥脆,好吃極了



“少年航天科普特訓(xùn)營(yíng)”舉行,VR空間站引關(guān)注
- “少年航天科普特訓(xùn)營(yíng)”舉行,VR空間站引關(guān)注
- 江西加速布局VR產(chǎn)業(yè) 引進(jìn)國(guó)內(nèi)外VR領(lǐng)域人才
- 曾國(guó)藩故居首次推出VR全景展館
- 上海浦東:人工智能當(dāng)幫手 辦事效率快又好
- 結(jié)合VR(虛擬現(xiàn)實(shí))互動(dòng)技術(shù) 打造線上老博會(huì)虛擬展館
- “5G+VR” 身臨其境感知革命文物價(jià)值
- 消費(fèi)促進(jìn)月系列活動(dòng)之一“龍江云展會(huì)”
- VR產(chǎn)業(yè)迎來發(fā)展熱潮
- 應(yīng)時(shí)而謀 搶抓機(jī)遇 如何加快推動(dòng)VR產(chǎn)業(yè)發(fā)展?
- “讓歷史說話 讓文物開口!”
- 貸款利息如何計(jì)算?貸款還款時(shí)間可以改嗎?
- 恩格爾系數(shù)是什么?恩格爾系數(shù)和基尼系數(shù)有什么區(qū)別?
- 換手率多少最合理?換手率高說明什么?
- 通縮和通脹有什么區(qū)別?通縮對(duì)老百姓意味著什么?
- 大額存單多少起存?大額存單和定期存款有什么區(qū)別?
- 期權(quán)組合有哪些?期權(quán)和期貨區(qū)別有哪些?
- 北交所如何開通?北交所適合散戶嗎?
- 存單變保單能取出來嗎?銀行保單有風(fēng)險(xiǎn)嗎?
- 預(yù)期年化收益率怎么算?年化收益率和年利率區(qū)別有什么?
- 金融業(yè)包括哪些行業(yè)?金融降薪意味著什么?
- 生化危機(jī)5如何保存?生化危機(jī)游戲共幾部?
- 魔獸世界日常任務(wù)有什么?魔獸世界什么時(shí)候出的?
- CF游戲截圖保存在哪里?CF是什么意思?
- 體育賽事行業(yè)規(guī)模持續(xù)增長(zhǎng) 電子競(jìng)技類專業(yè)引人注目
- 國(guó)內(nèi)游戲版號(hào)停發(fā)超半年 游戲出海成行業(yè)發(fā)展重點(diǎn)
- 電競(jìng)行業(yè)壓力大,看電競(jìng)選手的苦與樂
- 我國(guó)建立首個(gè)游戲音頻設(shè)計(jì)與開發(fā)流程團(tuán)體標(biāo)準(zhǔn)
- 游戲裝備可被繼承 虛擬財(cái)產(chǎn)不“虛無”
- 國(guó)風(fēng)游戲?yàn)橹袊?guó)電影“出海”開辟新路徑
- 電競(jìng)有無限的機(jī)會(huì)和可能
- 手游行業(yè)迅速發(fā)展 游戲?qū)κ謾C(jī)性能的需求不斷飆升
- 原汁原味懷舊版 點(diǎn)燃青春記憶
- 玩游戲成新一代社交方式
- “宅經(jīng)濟(jì)”風(fēng)口 助推中國(guó)游戲“出海”新路徑
- 提高安全警惕 謹(jǐn)防手游網(wǎng)游詐騙
- 中國(guó)互聯(lián)網(wǎng)大會(huì)在線互動(dòng)體驗(yàn)展
- “玩”出出息 “玩”出將來
- 天天象棋殘局挑戰(zhàn)190期詳細(xì)攻略
- 手游《慶余年》“逢君測(cè)試”已經(jīng)落下帷幕
- 《尋道大千》守衛(wèi)修真世界和平 齊心協(xié)力面對(duì)威脅